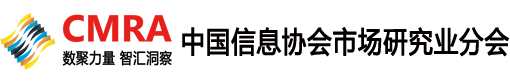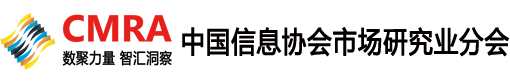摘要
视频广告是最重要的广告形式,而在移动互联网上有不同的广告媒体场景。典型场景包括视频APP中作为前贴片播放和在微信朋友圈中作为信息流视频播放。两者的效果是否一致?影响效果的因素有哪些?针对这些问题,本研究提出了一个媒体场景力模型,结合传统问卷方法和神经科学手段,对典型移动互联网场景下的视频广告价值进行了评估。结果反映,朋友圈用户相对于视频APP用户而言,在场景中的目的性较低。朋友圈中的视频广告播放时,能引发更加积极的情绪反应。在无强行播放的前提下,朋友圈视频广告的可见度,与视频APP中强行播放的视频广告的可见度持平。传播效果方面,朋友圈视频广告的品牌回忆、喜爱度效果均高于视频APP中的广告。研究表明,场景的不同使得广告引发的用户实时心理反应不同,最终造成了广告传播效果的不同。视频广告的价值因场景的不同而存在差异。
关键词:视频广告;价值;媒体;场景;眼动;脑电
Abstract
Video advertising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orms of online ads, and there are different media contexts on the mobile internet. Typical contexts include video APPs where ads are pre-rolls and WeChat Moments where ads are In-Feed videos. Do these ads obtain same effectiveness? What a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Targeting these questions, this study proposed a Scenario Power Model and utilized questionnaire and neuroscience methods to evaluate the value of video ad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users of Moments are less goal-directed than the video APP users. When played in Moments, ads evoked more positive emotion of the users. Being viewed voluntarily, ads in Moments gained a visibility as high as that of the ads in the APP, which were non-skippable. As for communication effectiveness, ads in Moments performed better in brand recall and ads liking. Our study suggests that differences in the contexts bring the disparities in users’ psychological responses toward the same ad, thus making the ad’s effectiveness different. Therefore, the value of video advertising depends on media context.
Keywords: video advertising, value, media, context, eye-tracking, EEG
1研究背景
1.1现实背景
近年来视频营销对于企业的价值日益凸显,视频广告投放持续增长。2014年,由Millward Brown发布的《视频广告投放趋势洞察》白皮书显示,视频广告已成为广告主最青睐的网络广告投放形式【1】。根据艾瑞咨询发布的《2016Q1网络广告行业报告》,2016年1季度中国网络广告季度市场规模达543.4亿元,其中视频广告所占比例达到历史新高的10.1%【2】。视频广告的载体也即媒体平台,包括了电视视频广告、移动视频广告、PC视频广告、户外视频广告、跨/多屏视频广告和VR视频广告等,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
对视频广告而言,其所在媒体的场景对广告效果有着重要影响。奥美集团(Ogilvy Group)的副总裁Rory Sutherland认为:“场景对广告主决策的影响,远胜于我们所意识到的程度。”针对媒体场景与广告效果这一议题,英国卫报(Guardian)针对超过300品牌营销活动的调查研究发现,媒体场景对于广告的作用是显著的【3】。特定媒体场景与其中广告的创意、投放形式是否匹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广告效果发挥。因此,为了优化广告投放的形式和创意、进行广告投放创新,媒体场景对于视频广告的赋能效力及广告的价值,都需要得到客观准确的评估。而近年来,为了更深刻地洞察消费者,业界开始应用各类认知神经科学手段。神经营销学(neuromarketing)方法被广泛地运用于广告研究主题中,成为了理解消费者在媒体场景下的广告反应的有力工具(张子旭 2011; Plummer et al. 2007)。
1.2理论背景
理论界对于媒体的场景问题,也展开了一定的探索。场景(Context)被认为是媒体的一种属性。De Pelsmacker等(2002)将媒体场景定义为:个人所感知到的、广告所置入的媒体内容的特征(De Pelsmacker, Geuens, and Anckaert 2002)。从用户心理的视角来看,场景被认为能给用户带来一种体验,这种体验可以是实用的(utilitarian)也可以是享乐的(enjoyable)(Calder, Malthouse, and Schaedel 2009);场景也因具备情绪属性而被认为能引发用户的情绪反应(Coulter 1998)。
在媒体和广告的关系研究中,场景对广告的影响一直是最重要的议题之一(Yi 1990)。前人发现,媒体场景在广告回忆与再认、广告信息处理的水平和方式、广告态度和认知、品牌态度和购买意愿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影响(Dahlén 2005)。已有研究认为,场景与广告之间存在着匹配问题,特定的场景对于特定形式的广告是合适的(如:Perry et al., 1997)。还有研究者明确指出,在对“场景如何影响人们对于广告的反应”这一问题具备了一定的了解时,恰当地利用媒介场景,便成为广告投放者能够有力控制的一种提升广告效果的方法(Calder, Malthouse, and Schaedel 2009)。
2研究问题与假设
2.1问题提出
在当前互联网时代视频广告迅速增长、多屏多应用平台场景各异的背景下,针对视频广告及其媒体场景需要评估的现实需求,本研究力图从场景角度来探索视频广告的价值评估。基于对前人理论研究的梳理和总结,本文认为场景的心理因素是场景特征的最典型表现,场景心理对广告效果的影响机制是理解场景力的关键。由于媒体场景心理的差异,场景对视频广告的赋能能力有所不同,广告最终实现的价值也不同。
具体地,本研究将在前人的研究和实践基础上进行拓展,对研究对象——微信朋友圈和视频APP中的视频广告价值——进行评估。视频APP是视频广告投放的传统主力阵地,互联网广告中的视频贴片广告在2015年所占比例达8.2%【4】。而朋友圈作为一种新兴的广告媒体,自2015年1月开始投放第一批信息流(feed)商业广告以来【5】,仍处在快速发展中。朋友圈本身作为一种社交平台,在用户规模、用户黏性、用户使用习惯、社交互动模式和平台内容等方面有着鲜明特征。但朋友圈作为视频广告的投放媒体,它具备怎样的场景心理特征、场景下用户对原生(native)视频广告的反应如何、场景对广告的传播效果如何赋能,这一媒体中的视频广告与传统视频APP中的视频广告价值差异如何,是仍需要解答的问题。因此,本文将使用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并结合市场研究经典方法和认知神经科学工具,对微信朋友圈和视频APP的媒体场景心理特点及其中原生视频广告发挥的效果进行对比性的测量,从而对其中视频广告的价值进行评估。
2.2媒体场景力模型
本文基于已有理论和实践提出一个媒体场景力的框架。在这一框架下我们认为,媒体场景心理是媒体作用于广告的重要因素。在一定的场景设计下,场景会呈现出特定的心理层面的特征;置于场景内的具有特定形式和创意的广告,会得到用户的加工处理,从而激发用户一系列的实时心理反应,广告对用户产生的这类作用即为广告引力;最终,由于广告对用户所产生的引力不同,广告所达到的传播效果存在差异,广告的价值也就各有不同。
基于此框架我们还认为,场景与广告是否匹配,取决于在特定场景心理下,广告是否能产生强的引力,从而发挥最优的效果。为了提升广告传播效果,需要进行媒体场景的优化决策,其中包括了场景的设计改进、广告创意/形式与场景的匹配度提升等策略。
2.2.1场景心理
在已有从心理角度对媒体场景进行的相关研究中,有两个心理维度受到研究者的关注:目的性和情绪。研究者们针对这两个维度与广告之间的关系分别进行了探索,并证明了它们的重要程度。因此,本研究提出场景心理是一个包含了目的性和情绪在内的二维因素。
目的性这一变量从人类信息搜寻行为的研究中衍生而来,在互联网时代被认为是浏览模式上的特征,并被认为是媒体使用上的一种认知属性。目的性的强弱,指的是用户使用媒体时是否有明确的目的导向(goal-directed)(Humphreys, Von Pape, and Karnowski 2013)。已有互联网行为研究中,基于目的性对于信息加工的影响,讨论了该因素与用户的广告反应/广告效果之间的关系。研究者认为,在目的性强弱不同的互联网使用模式下,用户对于外界信息——特别是新颖的变化的信息——的处理方式是不同的(Pagendarm and Schaumburg 2001)。Hupfer & Grey基于交互广告模型(Interactive Advertising Model, IAM)(Rodgers and Thorson 2010)指出,用户对于广告的反应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信息获取模式。目的性强的信息获取意味着置于广告上的认知努力会更少(Hupfer and Grey 2010)。Cho & Cheon则提出,当互联网用户觉得广告干扰了他们的目的实现时,对广告的回避会更强烈(Cho and Cheon 2004)。传播效果方面,有研究发现,任务导向很强的时候,用户更加回避广告,时候对广告的回忆和再认也更弱(Hershberger and Costea 2002; Danaher and Mullarkey 2003)。
媒体场景中的情绪变量在已有研究中也被大量探讨。在媒体这一范畴内讨论的情绪,其本质与大多数情绪研究中所定义的一致,从效价维度上来说可分为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Bradley and Lang 1994)。但本文中讨论的情绪,与已有若干研究一致,指的是用户在媒体使用中基于(也许是无意识的)对整体体验的评估而形成的情绪(Wirth and Schramm 2005; De Pelsmacker, Geuens, and Anckaert 2002),而并非是媒体中某一特定内容刺激带来的瞬间情绪。媒体场景通常能使用户体验到一系列的情绪(Puccinelli, Wilcox, and Grewal 2015)。与目的性维度相似的是,情绪也被认为是通过影响信息加工处理来影响广告效果的(Shapiro, MacInnis, and Park 2002; Wirth and Schramm 2005)。例如场景情绪的积极或消极,会影响说服性信息的加工路线(Petty and Cacioppo 1986),从而影响广告的效果(Bless et al. 1990; Schwarz 2012; Aylesworth and MacKenzie 1998)。另外场景情绪也会对广告加工中的情绪产生影响,从而改变广告的效果(Goldberg and Gorn 1987)。具体研究则发现,场景中的情绪会影响用户对广告的态度、喜爱度和回忆等。积极的情绪将导致更积极的广告态度、更高的喜爱度和更强的回忆(Goldberg and Gorn 1987; Aylesworth and MacKenzie 1998; Coulter 1998; De Pelsmacker, Geuens, and Anckaert 2002)。
2.2.2广告引力
本研究认为,场景中广告所引发的用户加工过程中的实时心理反应体现了广告的引力。其中两个关键维度分别是注意和动态情绪。与前人从效果角度对于互联网广告所带来的心理反应进行讨论(陈芒 2007; 唐艳梅 2007),或从利益角度定义引力(Yang 2004)有所不同,本文认为为了更加客观地评估视频广告、提升测量指标的可预测性,应当将广告所引发的用户即时心理反应作为引力的内涵。因此,本研究模型中的广告引力反映的是过程性而非结果性的心理反应。
注意和动态情绪,在已有广告研究中是最常见的议题(Heath, Brandt, and Nairn 2006; Hollis and Brown 2010)。例如:Teixeira指出,从传播沟通角度来说,注意力是广告发挥说服力的必要条件(Teixeira 2014)。Mehta & Purvis曾整合多项研究,系统地讨论了广告引发的注意和情绪对于广告再认和喜爱度的显著作用,并提出注意的长度和深度决定了记忆的形成(Mehta and Purvis 2006)。Anastasiei & Chiosa研究了人们对于广告的情绪反应,认为情绪可以直接作用于人们的广告态度、品牌态度和购买意愿,也可以通过调节认知、改变信息处理来影响广告再认等。他们的实证研究反映出情绪的效价(积极/消极)是对广告效果最具解释力的维度(Anastasiei and Chiosa 2014)。Batra & Ray也发现了广告引发的情绪会作用于广告态度,从而进一步作用于品牌态度和购买意愿(Batra and Ray 1986)。Chan & Kim则在对动态banner广告的研究中明确指出,广告引发的消极情绪会导致消极的广告态度(Chan and Kim 2005)。同时也有学者特别提出,对于电子媒体来说,广告的情绪反应对于广告效果的作用力更突出(Chaudhuri and Buck 1995)。
因此,本研究模型中的广告引力针对广告处理过程中最关键的两个维度——注意和动态情绪——进行考量,从而力求获得用户对广告进行加工的过程中的主要心理反应。注意,考虑的是用户对于广告投入注意资源的程度;动态情绪,指向用户加工过程中由广告引发的情绪效价。
2.2.3传播效果
对处在媒体场景中的广告进行评估,从而对媒体以及广告价值进行评估,需要选择关键的效果变量。相对于一般的信息传播活动而言,广告的传播还需追求传播作用于消费者心理系统后引起各种心理上的变化(张芳 2007)。本场景力模型考虑的传播效果因素,包含了两方面的心理效果:认知和情感效果。具体来说,认知效果通过品牌回忆测量,而情感效果通过广告观看喜爱度测量。
2.2.4模型小结
本研究提出的完整场景力模型如图1所示。这一模型包含了场景心理、广告引力和传播效果三个因素。其中场景心理会影响置于其中的广告的引力,从而影响最终的传播效果。不同的媒体场景心理特点各异,置于其中的广告引力也会体现出差别,从而广告起到的传播效果也会不同。
在这一框架下,场景心理由一定的场景设计所决定;在同样的场景下,不同的广告引力各异,这种差异会由广告的形式和创意引起;传播效果则是由媒体场景对广告的赋能作用产生。根据传播效果,可以评估广告的价值、检验媒体场景与广告的匹配程度,并对媒体场景设计和广告的形式/创意提升提供参考。
图1:媒体场景力模型——场景心理、广告引力和传播效果之间的关系
2.3研究假设
基于前文所提出的媒体场景力模型,结合已有相关理论研究成果,我们对于媒体对视频广告的赋能效力提出若干假设。基于已有研究,我们认为视频广告投放媒体的目的性和情绪是场景心理的两个重要变量,它们对于广告引力的作用方式不同。强的目的性会阻碍视频广告实时引力的发挥,包括广告引发的注意和动态情绪;而积极的情绪则会提升广告引力。广告引力对传播效果的作用则表现为:注意和动态情绪都会对认知和情感这两方面的传播效果发挥影响,且这种影响都是正向的。具体来说,我们提出以下假设及子假设。
H1:场景心理不同的媒体中,同样的视频广告会发挥不同的广告引力。
H1a:场景心理中的目的性越强,视频广告引起的注意越弱。
H1b:场景心理中的目的性越强,视频广告引起的动态情绪越消极。
H1c:场景心理中的情绪越积极,视频广告引起的注意越强。
H1d:场景心理中的情绪越积极,视频广告引起的动态情绪越积极。
H2:视频广告对用户产生的广告引力不同时,广告的传播效果会有差异。
H2a:视频广告引起的注意越强,广告获得的认知效果越好。
H2b:视频广告引起的注意越强,广告获得的情感效果越好。
H2c:视频广告引起的情绪越积极,广告获得的认知效果越好。
H2d:视频广告引起的情绪越积极,广告获得的情感效果越好。
3实证研究
3.1研究案例简介
本研究目的在于对视频APP和微信朋友圈的视频广告价值进行评估和对比。我们选取某典型手机视频APP和微信朋友圈作为比较研究对象,结合实验和问卷的方法,测量两种媒体的场景心理特征以及视频广告在场景下的引力和传播效果,并进行比较分析。在研究中,我们分别模拟了真实环境下使用微信朋友圈(以下简称朋友圈)以及视频APP(以下简称APP)的情景,并在其中置入了与真实情景一致的视频广告。在参与研究的被试使用朋友圈或APP的过程中,记录他们眼动和脑电反应,并通过问卷追踪进一步获得被试的自我报告数据。
3.2研究方法
3.2.1研究样本
本研究样本共计100名,均来自北京地区。实验前,利用筛选问卷获得被试使用朋友圈或APP的行为习惯,并将被试分配至对应组。朋友圈的被试每天浏览朋友圈2-3次的占30%,4-5次的占42%,6次及以上的占28%。APP的被试中,每天使用APP观看视频1次及以下的占6%,2次的占40%,3次的占30%,4次及以上的占24%。朋友圈组有1名被试脑电数据噪音较大,未达到分析标准,因此数据未进入分析。最终有效被试共计99名(朋友圈组49名)。两组被试的人口统计学数据如表1所示。
表1:被试的人口统计学变量
|
组别
|
年龄分布(%)
|
性别比例(%)
|
|
25-30
|
31-35
|
36-40
|
41-45
|
男
|
女
|
|
微信朋友圈
|
32.65
|
25.53
|
24.49
|
16.33
|
44.9
|
55.1
|
|
视频APP
|
22
|
36
|
22
|
20
|
46
|
54
|
3.2.2实验过程
在实验中,被试被邀请至一间舒适的、模拟日常家居环境的房间中参与实验,由访问员引导整个实验流程。首先,访问员向被试简单介绍实验流程,为被试佩戴好测量设备并进行调试。接着,被试使用实验测试手机,浏览朋友圈或者使用APP。最后,由访问员就问卷各题项向被试提问,并记录回答。
为更好地模拟媒体的现实广告投放并避免广告本身特征的干扰,本研究用到了4支视频广告材料,时长均为15秒。其中三支为目标广告,用于两个媒体;APP中另使用一支非目标广告。在朋友圈和APP中,分别投放了一支和四支广告。实验从三支目标广告中随机选择一支呈现于朋友圈,并出现在被试打开朋友圈后的第五条。APP中的四支广告以前贴形式呈现,在正式视频内容前以随机顺序播放。
朋友圈组被试,在已经登录自己微信账号的测试机上,按照个人意愿自由浏览朋友圈内容,并可在任意时间结束浏览。APP组被试,在测试机上模拟某视频APP的环境下,点击观看带有前贴广告的某电视剧视频片段。
3.2.3测量工具与技术
本研究使用的测量方法包括3类:眼动、脑电和问卷,分别针对模型中各因素下的变量进行测量。
眼动和脑电测量的是场景心理中的情绪变量,以及广告引力中的注意和动态情绪变量。我们基于数字新思(Xinsight)的情感云平台(数字新思,北京),采用Eye Tribe Tracker Pro(The Eye Tribe,哥本哈根)眼动仪和Muse(InteraXon,多伦多)头带式便携脑电仪分别采集被试的眼动和脑电数据,并使用情感云平台进行数据的预处理。测量工具如图2所示。
图2:眼动和脑电测量情景示意图
其中,眼动仪会记录眼球典型运动之一:注视(也即眼球中央窝视野在目标上保持一定的时长的现象)。注视数据经过预处理,得到注视时长、可见和关注这三个属于广告引力的注意变量。注视时长,反映的是被试对刺激材料中特定兴趣区域(Area of Interest,AOI)所有注视持续时间的总和(单位:秒);可见指的是在兴趣区域是否有注视(0:否;1:是),可见度指的是在兴趣区域有注视的人数占所有人数的比例;关注指的是在兴趣区域是否至少有5次注视(0:否;1:是),关注度指的是在兴趣区域有至少5次注视的人数占所有人数的比例。
脑电仪则记录10-20国际电极位系统中的AF3、AF4、T9和T10四个电极点的脑电信号,并可输出各点在各脑电波频段的能量值。数据由情感云平台处理后,得到情绪指数,反映的是被试情绪的积极/消极性特征。一般来说,该指标与情绪的积极程度正向关联,值越大表明情绪越积极。指标为正时,情绪体现为积极正面;指标为负,则情绪体现为消极负面。情绪指数在本研究中用来测量场景心理中的情绪变量和广告引力中的动态情绪变量。
问卷则针对模型中的场景心理和传播效果两个因素进行测量。首先,利用李克特(Likert)10分量表测量被试使用某个媒体的目的性强弱(1:完全没有目的;10:有明确目的);基于积极消极情绪(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hedule,PANAS)模型(Watson, Clark, and Tellegen 1988; Watson and Clark 1999),利用李克特5分量表测量被试使用某个媒体的愉快/感兴趣/放松/集中程度(1:一点也没有;5:非常多),这些均属于场景中的情绪变量。其次,传播效果中的品牌回忆变量,指的被试是否答出所观看的某支广告的品牌(0:否;1:是);广告观看喜爱度变量,是指利用李克特5分量表测量被试使用某媒体时,有多喜欢看到其中的广告(1:非常不喜欢;5:非常喜欢)。
3.2.4数据处理和统计
本研究将实验过程中获取的数据分为广告阶段的数据和场景阶段的数据。对于朋友圈组,广告阶段指的是广告信息从开始出现在屏幕上到完全退出屏幕的时间段;场景阶段则是广告出现前后最长各30秒,共计最长60秒的时间段。对于APP组,广告阶段指的是前贴广告的60秒时间段,场景阶段则是广告后正式视频播放的前60秒时间段。对于问卷测量的场景目的性、场景情绪和广告观看喜爱度,计算各组被试得分算数平均值;对于眼动测量的可见、关注,问卷测量的品牌回忆,计算值为1的比例作为均值;对于场景和广告阶段的脑电情绪指数,计算在各阶段内的平均值。
基于实验主要关注因子”媒体“的两个水平(朋友圈 vs. APP),本研究对于各变量在两个媒体中的均值及其间的差异,以及两个媒体内部场景情绪和广告情绪的脑电指数差异,使用SPSS20.0(IBM,阿克蒙)进行统计。对于0-1分布的变量(包括眼动的可见、关注,品牌回忆),采用卡方(χ2)检验来比较均值。对于非0-1分布的其它变量,先通过Shapiro-Wilk(W)检验进行正态分布检验。对于其中正态分布的变量,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均值;对于非正态分布的变量,采用非参数检验中的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均值。所有统计检验的显著性水平取0.05。
3.3数据结果
对非0-1变量是否为正态分布,进行Shapiro-Wilk(W)检验。结果表明,脑电测量的场景情绪指数(p=0.133)和广告情绪指数(p=0.342)符合正态分布假设,而其余变量均不符合正态分布(除场景目的性p=0.01,其余ps=0.000)。两种媒体中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以及均值比较的检验如表2所示。
表2:两种媒体中各变量的测量值及均值比较检验结果
|
模型因素
|
测量变量
|
朋友圈
|
视频APP
|
均值比较检验量
|
均值比较检验值
|
显著性水平
|
|
场景心理
|
目的性
|
5.061±1.853
|
7.460±2.022
|
Mann-Whitney U
|
Z=5.735
|
0
|
|
愉快
|
3.408±0.956
|
3.660±0.823
|
Mann-Whitney U
|
Z=1.208
|
0.227
|
|
感兴趣
|
3.520±0.931
|
3.347±0.779
|
Mann-Whitney U
|
Z=1.186
|
0.236
|
|
放松
|
3.816±0.882
|
3.780±0.910
|
Mann-Whitney U
|
Z=-0.236
|
0.813
|
|
集中
|
3.327±0.747
|
3.600±0.857
|
Mann-Whitney U
|
Z=1.661
|
0.097
|
|
脑电情绪指数
|
0.486±9.861
|
-1.876±13.157
|
T
|
t(97)=1.007
|
0.315
|
|
广告引力
|
可见度
|
0.980±0.143
|
0.980±0.085
|
χ2
|
χ2(1)=0.337
|
0.561
|
|
关注度
|
0.674±0.474
|
0.865±0.243
|
χ2
|
χ2(1)=9.613
|
0.002
|
|
注视时长
|
5.586±8.340
|
8.086±4.281
|
Mann-Whitney U
|
Z=4.206
|
0
|
|
动态情绪
|
4.158±12.491
|
-1.598±13.200
|
T
|
t(97)=2.228
|
0.028
|
|
传播效果
|
品牌回忆
|
0.551±0.503
|
0.380±0.312
|
χ2
|
χ2(1)=4.746
|
0.029
|
|
广告观看喜爱度
|
3.367±0.782
|
2.740±0.944
|
Mann-Whitney U
|
Z=-3.221
|
0.001
|
此外,针对两种媒体分别比较内部场景情绪和广告情绪的脑电指数差异,T检验结果显示:朋友圈用户看广告时的情绪(均值=4.158,标准差=12.491)相比场景中的情绪(均值=0.486,标准差=9.861)有了显著提升(t(48)=2.085,p=0.042),但视频APP用户看广告时的情绪(均值=-1.598,标准差=13.20)与场景中的情绪(均值=-1.876,标准差=13.16)无显著差异(t(49)=0.250,p=0.803)。
4研究结论与讨论
4.1研究结论
4.1.1基本结论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作为视频广告媒体,朋友圈相对于APP使用目的性更弱,而两者在情绪的积极/消极程度上并没有显著差异。两种媒体的场景心理差异主要凸显在目的性上。两种媒体的场景心理特征如图3所示。
图3:微信朋友圈和视频APP的场景心理
在观看媒体中的视频广告时,朋友圈用户和APP用户在”会看到视频广告“上的几率相同,且几乎接近百分之百。从”关注地看广告“上的几率和关注时长上来说,APP用户更有可能关注到广告,看某一条视频广告的时间也会更长。而视频广告在不同媒体场景下引发的用户情绪反应差异显著,朋友圈中视频广告所引发的用户情绪为积极情绪,APP中视频广告引发的是消极情绪。因此,两种场景下的广告引力表现不同,APP中视频广告更会被专注和长时间观看,而朋友圈中视频广告能激发用户更积极的情绪反应。广告引力的差异见图4。
图4:微信朋友圈和视频APP的广告引力差异
在视频广告的传播效果方面,朋友圈场景下广告体现了更佳的传播力。首先,品牌回忆上,朋友圈用户更多地回忆起了广告中的品牌;其次,朋友圈用户在使用中观看广告时的喜爱程度显著高于APP用户。传播效果上的媒体差异如图5所示。
图5:微信朋友圈和视频APP的传播效果差异
基于以上结果,本研究假设得到验证的情况如表3所示。
表3:研究中各假设的验证情况
|
假设
|
验证情况
|
|
H1:场景心理不同的媒体中,同样的视频广告会发挥不同的广告引力。
|
部分验证
|
|
H1a:场景心理中的目的性越强,视频广告引起的注意越弱。
|
未被验证
|
|
H1b:场景心理中的目的性越强,视频广告引起的动态情绪越消极。
|
被验证
|
|
H1c:场景心理中的情绪越积极,视频广告引起的注意越强。
|
未被验证
|
|
H1d:场景心理中的情绪越积极,视频广告引起的动态情绪越积极。
|
被验证
|
|
H2:视频广告对用户产生的广告引力不同时,广告的传播效果会有差异。
|
部分验证
|
|
H2a:视频广告引起的注意越强,广告获得的认知效果越好。
|
未被验证
|
|
H2b:视频广告引起的注意越强,广告获得的情感效果越好。
|
未被验证
|
|
H2c:视频广告引起的情绪越积极,广告获得的认知效果越好。
|
被验证
|
|
H2d:视频广告引起的情绪越积极,广告获得的情感效果越好。
|
被验证
|
4.1.2结果讨论
微信朋友圈和视频APP两种媒体,一种具有极强的熟人社交属性,一种是内容为主的娱乐性平台。两个媒体场景中的信息类型和呈现形式有着巨大的差别。同样是主要在休闲时间被使用的媒体,用户在使用时的需求也不同。因此,作为视频广告媒体,两者呈现出了不同的场景心理特征,这种不同主要体现在了用户目的性的强弱上。用户使用朋友圈时,目的性很弱,而使用视频APP时有很强的目的性。我们认为这主要是两种媒体信息形式和功能属性的差别所导致的。朋友圈中的信息形式多种多样,原生内容包括用户好友发布的原创文字、图片、小视频以及好友转发的导向各类内容的链接;视频APP中的信息以视频为主,原生内容主要是用户关联程度不大的各类账号发布的各种视频。朋友圈主要作为用户的社交工具;视频APP主要作为用户观看视频的平台。所以,用户在使用朋友圈时,有的是一种模糊的社交诉求,难以预计自己将要看到何种信息,也更难有完成某种任务的明确目的;但在使用视频APP时,通常是为了观看某个或某种自己有兴趣的视频,即使是无明确观看目的时,也会有较为清晰的信息搜索目的(“找到自己想看的”)。已有研究表明,场景心理会对广告信息加工过程产生影响(Moorman 2003),包括注视、知觉、信息存储、情感/认知反应等心理过程(裴杨 2012)。其中有研究指出,使用互联网时的目的性强弱,影响了用户对新颖信息的处理方式,目的性弱的情况下用户会更容易对新颖变化的信息进行“自下而上”的处理(Pagendarm and Schaumburg 2001)。这种加工方式下,人们的知觉主要基于外部的刺激而更少地基于已有的观念,对信息的加工深度会更强。在视频APP中,视频广告与原生内容的信息呈现形式一致;但朋友圈中,视频并不是原生内容的主要形式,视频广告相对于原生内容更可能是一种新颖的信息。因此,朋友圈用户在看到视频广告时,很可能更少地戴着“看广告”的有色眼镜来看广告,对广告的加工强度也可能更高。而由于用户使用朋友圈的目的不强,所以会更少地感觉到广告对目的实现的干扰,对广告的回避程度也会更弱(Cho and Cheon 2004; Danaher and Mullarkey 2003)。
基于媒体场景力模型,同样的广告在不同的媒体场景心理前提下,会造成用户不同的心理反应,实现不同的广告引力。事实上,对广告所引发的用户实时心理反应进行神经科学方法的测量后,我们发现,两种媒体下的视频广告导致的用户注意和动态情绪有着很大不同,即使实验在两种媒体平衡投放了同样的广告。在均能获得接近百分之百的可见度的前提下,视频APP中的广告获得的关注比例和注视时长更高,表明用户反复看了广告、看的时间较久。但考虑到两种媒体广告在广告可跳过性上的差别——视频APP中的广告为不可跳过而朋友圈中的广告并没有强制性,我们认为关注程度和注视时长的差异很可能是这个因素造成的。同时对脑电情绪指标的分析可以发现,朋友圈用户在看视频广告时处于积极的情绪状态;但视频APP用户则在看视频广告时表现出了消极的情绪。朋友圈中的视频广告并未像通常媒体中的广告那样让用户感受到厌烦,而是让用户产生了愉悦感。结合场景心理的特征,我们认为朋友圈场景的目的性弱,使得广告的侵入性(intrusiveness)弱(Hupfer and Grey 2010),用户的回避心态也弱。在看到视频广告这种较为新颖的信息时,即使加工时长较短,但加工意愿较强。为进一步观察场景造成的不同广告引力,我们对于两种媒体,将场景心理中的情绪和广告引力中的动态情绪分别进行均值比较。结果表明,朋友圈用户看广告时的情绪显著高于场景中的情绪,而视频APP用户看广告时的情绪相对于场景中的情绪并无差异。这说明,微信朋友圈的场景使得广告产生了较强的引力,给用户带来的是积极的感受,体现了朋友圈作为视频广告媒体的更强的实时赋能效力。
对广告的传播效果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微信朋友圈视频广告在认知和情感两个方面都实现了更好的心理效果。具体地,朋友圈中的广告更容易让用户回忆起来,更让用户觉得喜欢看。传播效果的结果表明,相比视频APP而言,朋友圈的心理场景通过提升视频广告的实时引力,最终提升了广告的传播效果。朋友圈中的视频广告价值更高。结合两种媒体场景下广告引力的差异我们认为,传播效果会受到广告引力中注意和动态情绪的影响,但两者的作用强度和作用方式也许不尽相同,情绪有可能是在传播效果提升上最为关键的因素。这也与前人对于注意和情绪对广告效果的影响的讨论一致(Heath, Brandt, and Nairn 2006)。
通过实验方式,结合神经科学的研究手段,我们利用媒体场景力模型对于微信朋友圈和视频APP两种媒体中的视频广告价值进行了测评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了两种媒体在场景心理上确实存在差异。当常见的短视频广告被置于不同心理的场景中,在注意和情绪两方面体现了不同的广告引力。最终对广告传播效果的考察,反映了广告在心理层面上的效果差异。这些结果,体现了不同媒体对于视频广告的赋能效力差异,也反映了不同媒体场景中视频广告的价值差异。因此,本研究在对媒体广告效果评估的探索上,追溯到了效果形成的广告加工过程上的原因、以及广告发挥效果的环境因素——场景。在媒体场景力框架下,实现了对视频广告的价值评估和比较,并且探索了媒体场景力实现的具体机制。基于这种机制,我们认为视频广告投放时,有必要将场景心理这一特征纳入考虑范围。另外,在特定媒体场景下,也可能会存在着一种或多种适合的广告形式/创意。所以,场景与广告之间的匹配性问题在本研究中得到了展现,媒体场景力模型也同时为匹配性的考量问题提供了一种研究框架。
4.2研究意义
4.2.1理论贡献
本研究提出了一个视频广告价值评估的“媒体场景力”模型,并在一个实证研究案例中对两种典型投放媒体中的视频广告进行了比较评估。研究在“媒体对广告效果的影响”这一主题的探讨中,聚焦于媒体场景,并从用户心理的层面上提炼了两个场景特征来构建媒体场景因素。对于场景心理与广告效果的关系,本研究通过观察广告在场景中引发用户心理反应的实时过程,探索了场景对广告产生作用的一种具体机制。在广告媒体分析和广告价值测评上,本文实现了一定的理论创新和拓展。
本研究在对模型变量的测量上,采用了问卷与认知神经科学工具的结合。一方面,对传统方法难以实时追踪的心理反应实现了测量;另一方面,也以实证研究验证了神经科学研究技术在广告媒体研究中的适用性,拓展了眼动和脑电两种营销研究前沿技术的应用主题。
4.2.2应用价值
本文在一个贴近现实的实验情境中评估了不同媒体中视频广告的表现,并提出了测评场景和广告的一种方法,因此对于媒体和广告的营销实践也具备现实意义。相比以往研究,本研究提供了一个覆盖实时效果观察、包括了行为/生理多维度指标的评估模型,可实现较为客观、准确的广告效果评估。从而我们认为,本文为营销界的实践者提供了测评广告价值的可行方法。
本研究的发现,也为广告主和媒体从业人员的广告投放决策和广告设计优化提供了参考。我们的结果表明,特定的媒体场景与一定形式和创意的广告之间存在着匹配的问题。通过对媒体特征和广告价值的测评,广告的投放和设计可基于匹配度的提升得到优化。
4.3未来展望
因时间、成本等因素限制,本研究在使用媒体场景力模型对视频广告价值进行评估时,只选择了某视频APP和微信朋友圈两种场景进行了比较,且仅探讨了典型的短视频广告。未来研究可以考虑通过媒体场景的视角对多个种类媒体、或同种类的相似媒体进行比较;另外,也可以评估同一媒体场景下何种广告形式或创意能发挥更高价值。我们也将在未来继续探索媒体场景心理与广告创意/形式等的匹配问题。
其次,本研究的样本选自北京地区且数量有限。研究结论的概化能力也需要在将来研究中进行验证。我们计划继续选取地理分布不同的更多样本来做进一步的研究。此外,未来研究也可以考虑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进行研究,观察场景心理的影响是否存在文化差异。
最后,本问模型中的场景心理因素构建可以做进一步的拓展。在模型中,可以引入更多有密切关联的场景心理变量,从而完善模型,提升模型的解释力和预测力。
参考文献
[1] Anastasiei, Bogdan, and Raluca Chiosa. 2014. “Emotional Response to Advertising.” EuroEconomica 2 (33): 43.
[2] Aylesworth, Andrew B, and Scott B MacKenzie. 1998. “Context Is Key: The Effect of Program-Induced Mood on Thoughts about the Ad.” Journal of Advertising 27 (2): 17–31. doi:10.2307/4189069.
[3] Batra, Rajeev, and Michael L. Ray. 1986. “Affective Responses Mediating Acceptance of Advertising.”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13 (2): 234. doi:10.1086/209063.
[4] Bless, H., G. Bohner, N. Schwarz, and F. Strack. 1990. “Mood and Persuasion: A Cognitive Response Analysi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doi:10.1177/0146167290162013.
[5] Bradley, M M, and P J Lang. 1994. “Measuring Emotion: The Self-Assessment Manikin and the Semantic Differential.” Journal of Behavior Therapy and Experimental Psychiatry 25 (1): 49–59. doi:00057916(93)EOO16-Z.
[6] Calder, Bobby J., Edward C. Malthouse, and Ute Schaedel. 2009.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nline Engagement and Advertising Effectiveness.” Journal of Interactive Marketing 23 (4). Direct Marketing Educational Foundation, Inc.: 321–31. doi:10.1016/j.intmar.2009.07.002.
[7] Chan, Yun Yoo, and Kihan Kim. 2005. “Processing of Animation in Online Banner Advertising: The Roles of Cognitive and Emotional Responses.” Journal of Interactive Marketing 19 (4): 18–34. doi:10.1002/dir.20047.
[8] Chaudhuri, Arjun, and Ross Buck. 1995. “Media Differences in Rational and Emotional Responses to Advertising.”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39 (1): 109–25. doi:10.1080/08838159509364291.
[9] Cho, Chang-Hoan, and Hongsik John Cheon. 2004. “WHY DO PEOPLE AVOID ADVERTISING ON THE INTERNET?” Journal of Advertising 33 (4): 89–97. doi:10.1080/00913367.2004.10639175.
[10] Coulter, Keith S. 1998. “The Effects of Affective Responses to Media Context on Advertising Evaluations.” Journal of Advertising 27 (February 2015): 41–51. doi:10.2307/4189090.
[11] Dahlén, Micael. 2005. “The Medium as a Contextual Cue: Effects of Creative Media Choice.” Journal of Advertising 34 (3): 89–98. doi:10.1080/00913367.2005.10639197.
[12] Danaher, Peter J., and Guy W. Mullarkey. 2003. “Factors Affecting Online Advertising Recall: A Study of Students.” Journal of Advertising Research 43 (03): 252–67. doi:10.1017/S0021849903030319.
[13] De Pelsmacker, Patrick, Maggie Geuens, and Pascal Anckaert. 2002. “Media Context and Advertising Effectiveness: The Role of Context Appreciation and Context/Ad Similarity.” Journal of Advertising 31 (2): 49–61. doi:10.1080/00913367.2002.10673666.
[14] Goldberg, Marvin E., and Gerald J. Gorn. 1987. “Happy and Sad TV Programs: How They Affect Reactions to Commercials.”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14 (3): 387. doi:10.1086/209122.
[15] Heath, Robert, David Brandt, and Agnes Nairn. 2006. “Brand Relationships: Strengthened by Emotion, Weakened by Attention.” Journal of Advertising Research 46 (4): 410–19. doi:10.2501/S002184990606048X.
[16] Hershberger, Edmund, and Anca Elena Costea. 2002. “Task Orientation and Ad Recall?: An Exploratory Study.” Advances in Marketing, Management and Finances: Proceedings of the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rketing, Management and Finances, 82–87.
[17] Hollis, N, and M Brown. 2010. “Emotion in Advertising: Pervasive, yet Misunderstood.” Millward Brown: Point of View. http://www.armi-marketing.com/library/Hollis_EmotionInAdvertising.sflb.pdf.
[18] Humphreys, Lee, Thilo Von Pape, and Veronika Karnowski. 2013. “Evolving Mobile Media: Uses and Conceptualizations of the Mobile Internet.”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8 (4): 491–507. doi:10.1111/jcc4.12019.
[19] Hupfer, Maureen E, and Alex Grey. 2010. “Getting Something for Nothing?: The Impact of a Sample Offer and User Mode on Banner Ad Response.” Journal of Interactive Advertising 6 (1): 105–17.
[20] Mehta, Abhilasha, and Scott C. Purvis. 2006. “Reconsidering Recall and Emotion in Advertising.” Journal of Advertising Research 46 (1): 49–56. doi:10.2501/S0021849906060065.
[21] Moorman, Marjolein. 2003. Context Conside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a Environments and Advertising Effect. Amsterdam: ASCoR.
[22] Pagendarm, Magnus, and Heike Schaumburg. 2001. “Why Are Users Banner-Blind? The Impact of Navigation Style on the Perception of Web Banners.” Journal of Digital Information 2 (1).
[23] Perry, SD, SA Jenzowsky, CM King, H Yi, JB Hester, and J Gartenschlaeger. 1997. “Using Humorous Programs as a Vehicle for Humorous Commercial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7 (1): 20–39. doi:10.1111/j.1460-2466.1997.tb02691.x.
[24] Petty, R.E, and J.T. Cacioppo. 1986. “The 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 of Persuasion.”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9: 123–83. doi:10.1558/ijsll.v14i2.309.
[25] Plummer, Joe, Bill Cook, Don Diforio, Bert Schachter, Inna Sokolyanskaya, and Tara Korde. 2007. “Measures of Engagement Volume II.” ARF II: 64. http://gandrllc.com/reprints/Measures_of_Engagement_Vol_II_Final_Paper.pdf.
[26] Puccinelli, Nancy M, Keith Wilcox, and Dhruv Grewal. 2015. “Consumers’ Response to Commercials: When the Energy Level in the Commercial Conflicts with the Media Context.” Journal of Marketing 79 (March): 1–18. doi:10.1509/jm.13.0026.
[27] Rodgers, Shelly, and Esther Thorson. 2010. “The Interactive Advertising Model: How Users Perceive and Process Online Ads.” Journal of Interactive Advertising 1 (1): 42–61. doi:10.1007/s00256-006-0137-x.
[28] Schwarz, Norbert. 2012. “Feelings-as-Information Theory.” In Handbook of Theories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ume 1, edited by P. Van Lange, A. Kruglanski, and E. T. Higgins, 289–308. 1 Oliver’s Yard, 55 City Road, London EC1Y 1SP United Kingdom: SAGE Publications Ltd. doi:10.4135/9781446249215.n15.
[29] Shapiro, S., D. J. MacInnis, and C. W. Park. 2002. “Understanding Program-Induced Mood Effects: Decoupling Arousal from Valence.” Journal of Advertising 31 (1998): 15–26. doi:10.1080/00913367.2002.10673682.
[30] Teixeira, T S. 2014. “The Rising Cost of Consumer Attention: Why You Should Care, and What You Can Do about It.” 14-055.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Working Paper. http://www.hbs.edu/faculty/Pages/item.aspx?num=46132.
[31] Watson, David, and Lee Clark. 1999. “The PANAS-X Manual for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hedule-Expanded Form.” Iowa Research Online 277 (6): 1–27. doi:10.1111/j.1742-4658.2010.07754.x.
[32] Watson, David, Lee Anna Clark, and A Tellegen. 1988.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Brief Measure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The PANAS Scal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4 (6): 1063–70. doi:10.1037/0022-3514.54.6.1063.
[33] Wirth, Werner, and Holger Schramm. 2005. “Media and Emotion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rends 24 (3): 2–44.
[34] Yang, Kenneth C C. 2004. “Effects of Consumer Motives on Search Behavior Using Internet Advertising.” CyberPsychology & Behavior 7 (4): 430–42. doi:10.1089/1094931041774668.
[35] Yi, Youjae. 1990.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Priming Effects of the Context for Print Advertisements.” Journal of Advertising 19 (2): 40–48. doi:10.2307/4188762.
[36] 陈芒. 2007. “基于心理过程的广告效果测评模型研究.” 大连海事大学.
[37] 裴杨. 2012. “名人代言人信息与认知需求对广告效果影响的眼动研究.” 杭州师范大学.
[38] 唐艳梅. 2007. “网络广告心理效果评估实证分析.” 广西大学.
[39] 张芳. 2007. “广告传播效果评估模型及其应用研究.” 四川大学.
[40] 张子旭. 2011. “神经科学与广告传播效果研究.” 国际新闻界 1.
【1】资料来源:http://www.madisonboom.com/2014/01/09/2014视频营销风向标:大剧、自制、创新广告齐头并/
【2】数据来源:http://report.iresearch.cn/content/2016/06/261636.shtml
【3】资料来源:http://www.campaignlive.co.uk/article/context-effect-right-environment-shape-ads-impact/1367958
【4】数据来源:http://report.iresearch.cn/content/2016/04/259999.shtml
【5】数据来源:http://ad.weixin.qq.com/
|